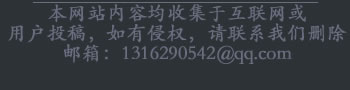首页 > 最新信息 / 正文
副标题:历史的绝响,是杨朱、阮籍、李商隐的哭
中国历史,风流辈出,风流者,风度、仪表,流风余韵,洒脱放逸,杰出不凡,格操映世,风韵倾国,风采特异……
而我于众多风流中,独钟情于三个彷徨歧路而哭的男人。
因为他们通古连今,有关生命探求与安顿,于特异的风采中,展现了生命的局限与辽远。
遭遇之下,他们只有心情的荒凉,而无心灵的荒凉,再难也不苟活,已俨然为历史的绝响。

(8000字,约需30分钟,慎入)
1
以前读史书,看到阮籍的哭,只觉得奇特,后来读了余秋雨《遥远的绝响》,才知道,这哭,原来很高远。
比如阮籍驾车载酒,荒野乱走,无路就哭,哭完再走,无路再哭这事,我本觉得这是迷茫的狂走,酒徒的作为,跟自己捣蛋的表现,抑郁症也说不定,但余秋雨只用一句“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,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,我们无法知道”,和一句“走一路哭一路,荒草野地间谁也没听见,他只哭给自己听”,就把我搞得很完蛋。
而他最令我震撼的,还是评说阮籍去哭兵家女孩的那一段。
那家人阮籍一个不认识,女孩也不认识,女孩的早逝本不关阮籍什么事,但阮籍一听到消息,就去了。自顾自地在灵堂大哭了一场。
对此,余秋雨说:
“这眼泪,不是为亲情而洒,不是为冤案而流,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速逝的生命。荒唐在于此,高贵在于此。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,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、太实在、也太自私了。
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,没有其他任何理由,只为美丽,只为青春,只为异性,只为生命,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。
依我看,男人之哭,至此尽矣。”
这让我由此也明白,或者说越发明白,人是不平等的,不同的学识、素养、心灵、情怀、情感,决定了理解、获得的不同,很多时候,书籍、人物、行为、事件、物品,是为对等的人准备的。
虽然我对于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某并无意见,对历史必然是客观、主观,真实、设定的结合、投射这一点也非常认同,甚至于因为脑子里有点“贵恙”,在此后仍旧还会莫名其妙地去开这样的脑洞:要是我跑去人家家里哭,到野外乱走、乱嚎,我现在一定一个朋友没有。
只在脂粉堆里厮混,正事一件没有的贾宝玉,在现实里只怕哪个爹都会将他暴打一顿,他也可能没朋友,但他在《红楼梦》,在文学、文化意象里却活得很逍遥,这大约是另一种不平等。
因此我有时候未免又怀疑阮籍之哭的真实性,觉得它只是一种意境。虽不至于像胡适怀疑屈原是否真正有过,顾颉刚怀疑大禹是否是条虫那么较真,但屈原《天问》的精神倒是有一点。
生命不止,追问不息嘛。
然而我最终当然也只好信其有。因为传说已成永恒,谁也无法更改,你可以保留你设问的权力,却没有更改的权力。而且,这已经是一种文化象征,符号性质的东西,大有益,我们也宁愿它有。我甚至觉得,这种历史细节的力量,才是历史真正的力量所在。
结果,逐渐地,我就发现,歧路之哭的祖师爷,原来不是阮籍,而是“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,取一毫而损天下亦不为”的杨朱,这之后他们还“带坏”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商隐,弄得他“东西南北皆垂泪”。男人之哭,既非始于阮籍,也非至阮籍而尽。
更重要的是,我们现在的一切,都印有古人的指纹,他们那三哭,环绕千古,他们因承袭了历史、文化、生命的神秘、拷问、挣扎、冲突,果然是史上最伟大的迷惘者。

2
“杨朱泣歧路,墨子悲染丝。”这是阮籍《咏怀》诗的起首之句,它讲的是两个典故。
“杨朱泣路”,这说的是:
杨朱邻居家的羊丢了,找了许多人帮忙寻找,也曾请杨朱派出仆人。之后找羊的人回来,杨朱问,找到没有,邻居说没有。再问为什么,邻居说,我们这歧路太多,歧路又有歧路,根本没法找。
于是杨朱忽然就呆了,仿佛宝玉听了紫鹃那句“你妹妹要回苏州家去”一样,如遭雷击。他虽然没有到“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,口角边津液流出,皆不自觉”的地步,但话却不肯再说了,好多天都没笑面。这弄得家里人都好生奇怪,又不是你的羊!
他们当然不知道宝玉的命是黛玉,杨朱的命是路。
歧路者,岔道也,十字路口,虽东西南北皆可往,却可能根本无从选择。岔道而又岔道,想必杨朱家所在是一座天然迷宫,而人生所处,恰也是这样一座迷宫。
杨朱心中的“羊”也早就丢了啊,他也一直在寻,一直在歧路上徘徊。他那“羊”的跑丢,代表的当然就是生命方向丢失,他那歧路复歧路,代表的当然就是生命始终无处安置,无法安放。这种事可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忙。
于是杨朱有一天,就终于站在十字路口大哭起来,好一阵滂沱,以至水淹历史,让阮籍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张九龄、韦庄等等,无数文人,都爱拿他自比,拿他说事。
谁不彷徨,谁不迷失,谁不怅惘,谁不追寻,谁日子好过,谁问题解决了啊!人类的生命感、孤独感,天地的罗网,历史的厚重,就由此而来。
但它到底属于自觉的生命,伟大的心灵,是寻常人难有的歧路之哭,寻常人看到路口哭泣的杨朱,只会觉得他病的不轻。
“墨子悲丝”,这说的是:
墨子有一次见到染丝者,如同杨朱见到邻居“亡羊”一样顿悟,他说:“染于苍则苍,染于黄则黄。五入为五色,不可不慎也。非独染丝,治国亦然。”
丝织物染上什么颜色,就是什么颜色,人也一样。人人都既是丝织物,又是染丝者,互相间混不自觉,社会是个大染缸。当其时,战争频繁,礼崩乐毁,道德缺失,秩序混乱,人心如浮萍,人命如草芥,于是墨子便悲从中来。
他们这悲,这哭,当然既是为自己,也是为他人,为世界,抽象而具体,“荒唐”又实在,“自私”而高贵。
只不过墨子悲而不哭,兼爱,起而拯救、决战,披蓑戴笠,食粗粝,睡板床,摩顶放踵,做苦行僧,利天下而为之。他太强大,最实际,最理想,目标明确,没空停下脚步,没空伤春。
同样的环境,同样的基础,同样的忧愤,同样的深悲,同样的关怀,他与杨朱的区别,其实也来自他们不同的关注点,不同的投射方向。
杨朱贵生命,重个体,重自我,他认为道德、礼仪、制度之类都是后造的,附加的,都很扯,天下事都是它们搞坏的;天下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,我们就不该追逐富贵荣华、功名利禄、锣鼓秧歌、长命百岁,人都应该回归原始本真;我的生命我做主,我的命运我做主,我不强加什么给你,你也别强加什么给我,大家各行其是,连君主都让他滚蛋,这才是正事。
所以他的学说,其实是老子无为,庄子逍遥游那一类,他是因为太过极端,才被人当成自私、颓废、堕落的代表,痛加批判的。而孟圣当年的发难,自然就只有让他更入冷宫,独自辗转。
殊不知,一种学说的盛行必有它盛行的理由,战国时期,可是有一名言,“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”的,杨朱、墨子曾非此即彼,各领风骚好多年。更何况,出于忧愤,创造学说,本身就是为影响世人,就是利他行为,所以杨朱的境况,到后来未免就逐渐好转起来,尤其是近现代。
比如贺麟先生曾说:“不拔一毛以利天下,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他人,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,亦不损人以利己,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,而取其两端的中道。”
比如吕思勉先生曾说:“夫人人不损一毫,则无尧舜,人人不利天下,则无桀纣;无桀纣,则无当时之乱;无尧舜,则无将来之弊矣。故曰天下大治也。杨子为我说如此,以哲学论,亦可谓甚深微妙;或以自私自利目之,则浅之乎测杨子矣。”
这显然就是说,杨朱的学说,不是简单的自私为我,而是为救世,为天下大治,属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生命学、哲学范畴,有某种很奥妙的东西在,它与克己的、牺牲的、高尚的、纯粹的、飞扬的墨子学说有近乎一样的底色。而它们不久走向散淡的原因,则无非都由于太过极端、乌托邦。
如此说来,墨子是一个高尚的悲剧,杨朱何尝不是?世界是欲望的世界,生命是欲望的生命,文明是欲望的文明,人与人,人与世界的联系是异常紧密的,杨朱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学说是行不通的。于是他越行不通,就可能越极端,越极端,越行不通,就可能越失望,越焦虑,越忧愤,越悲哀。
可是他所关注、思考的,却还不只是社会、政治、人事,还有宇宙自然、天地万物,天理、天命,高而又高,玄而又玄,这一切虽都表现为生命强大的探求欲望,人类巨大的野心,澎湃的激情,但毕竟人生短促,人力有限,都解决不可能,穷尽更不可能。
现实的、理想的、过去的、将来的、人事的、天事的、政治的、生活的、自然的、情感的,等等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捉摸,难以解决,于是杨朱这种人类的极品,在焦灼之外,恐怕就一定还得加上一个气馁。
晋朝的美少年、玉人卫玠,岂是看杀?他本身就为了天地间的玄理殚精竭虑,形销骨立。他渡江之时的那句“对此茫茫,不觉百感交集”,原本就透着同样深重的怅惘与悲感。这既是关于他自身命运的,也是关于他所身处的世界的。
人类的探索从未停止,这不管是关于社会的,生命的,还是自然的,但我们现在的探索,更多表现在技术层面,古人的探索因其朴素、自然,没有技术屏障,反而充沛天地之间,表现在更为辽远的精神层面。我们在技术文明之下,早已失去了那种宏大的浪漫与想象力,只为肤浅的欲望而悲喜,它于我们自然是早已陌生的,我们或许就因此不能了解那种神秘的推动力、使命感,和形同崩溃的怅惘、深痛与深悲。
同样的痛苦与大悲,在一个集科学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、逻辑学家、实践家、救世主于一身的墨子身上,只怕同样深重,他有幸关注的不是个人、个体,和意旨更深的生命与命运。他的伟大在于此,他的失败在于此。而政治家加玄学家,既墨子又杨朱,既儒家又道家,既入世又出世,即建安风骨又魏晋风度的阮籍,当其时,由于只能悲哀地发现,这两条路都不通,自己既不可为,又不得不为,既死不了,又活不好,所以就更加有了哭泣的理由。
他已经不只是站在歧路而哭,而是路口都已消失,根本无路,只能乱撞。他甚至连哭,都只能在旷野之中,无人之处,怕风有耳朵。
他其实并非因为是心的主人,才只哭给自己听,因此阮籍的痛苦、悲哀与孤独,到此,就比杨朱更深了一步。他如果肯放过自己,原本可以活得很好的。
但是杨朱、阮籍之哭,到底政治性强了些,他们的生命里,也缺少了爱情色彩,因此他们的哭相比之下,就又都比李商隐差了一点。李商隐的那种哭,才真正通向远古,通向现代,连接天地,通向生命本身。

3
李商隐不但是文学史上一大秘,也是人间一大秘,他给后人带来无数猜测,无数歧义,从他那些晦涩暧昧神秘的无题诗来看,他可能也有意这么做。
我本身就搞不懂我自己,为什么要让你们搞懂我?你们本来就从来没懂过我,我为什么要指望你们懂我?
李商隐的一生,似乎都是由一场婚姻搞坏的,他靠令狐家提携、帮助,才得以科举及第,但是他却爱上了王茂元的女儿。很不幸,王茂元是令狐家的政敌,他的结婚,恰在令狐楚死后不久。
于是李商隐首鼠两端,见风使舵,忘恩负义,人格卑劣的帽子从此以后,就再也摘不掉了。激战的两党都觉得不齿,都不敢用他。即便他才华高绝,可以与杜牧合称“小李杜”,跟李白、李贺合称“三李”,跟温庭筠合称“温李”,也无济于事。
偏偏他还命运奇差,偶尔有几个人赏识他,也不是这个事那个事,这终于弄得他在官场上始终没有起色。
李商隐是为情而娶,并没有参与政争,跟老丈人、大舅子的关系也并不好,日子难过之时,他当然也曾做过自辩,但他的自辩根本没人理会。当时的人都看不好他,史书也从不说他好话,后来为他正名的却是王安石。
王安石看来看去,最后敲定,大秩序崩溃下,能坚持道德理想,对唐代文化、政治有大规划的,惟李商隐一人。他是晚唐政治秩序的开创者,而且还不居功,他也是晚唐唯一继承了杜甫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胸襟与抱负的人。
王安石一锤定音,趣事出现,这之后的文人竟连李商隐的那些情诗也非往政治上靠了,不达目的决不罢休,闹了很多笑话。此事直到近代的苏雪林写了一部《玉溪诗谜》,说那真不过就是些情诗而已,大家这才不那么累了。
但是皇帝的新衣脱下又怎么样呢?大家又都踩着苏雪林的脚印,把李商隐的诗尽往情字上靠了。诗人是真实与文学的诗人,李商隐与女道士、宫女的若干情事并无实证,但大家却都非常乐意相信。李商隐的情诗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男女,李商隐全是写他自己,于是李商隐摇身一变,就由无行浪子,又变成爱情专家、情圣。
原来,爱多少人无妨,爱女道士、宫女无妨,只要你有感人的诗句,那就都无妨成为情圣的,
可是真实的李商隐什么样呢?
绝对的真实,是不可能有的,但相对的真实,一定可以有。首先,李商隐肯定是有政治理想与抱负的,只可惜他一生都不得志。李商隐这条路的堵塞,不仅因为自身的厄运,还因为环境、情境的综合制约,甚至于神秘未知的自然之力,它们浓厚如雾,密结成网,笼罩一切,绝难冲突,于是李商隐当然就不免要将自身转向另外的安顿。
文学是一条出路,爱情是一条出路,宗教是一条出路,但是这些路又怎样呢?文学只是一种寄托,诗解决不了现实问题,有唐以来,诗人们只有一个高适过得滋润;爱妻很早就已经去世,人留不住,爱情也留不住;宗教有时候也很虚幻,不然李商隐不会又佛又道——这个世界上看上去竟没一样可靠。
一面怀有政治理想,一面对政治绝望的李商隐,其实对爱情的态度,也呈现出矛盾的两端,一面向往爱情的真实、永恒,一面却完全不信任。
韩凭的爱情故事感动中国,广为流传对吧?韩夫人自杀的青陵台在李商隐笔下巍峨、灿烂,他还曾称之为“万古贞魂倚暮霞”对吧?但是伟大的爱情象征说完,他又做了什么呢?他竟来了一句:“莫讶韩凭为硖蝶,等闲飞上别枝花”。
他早就“直道相思了无益”了啊,何曾只有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?
钱牧斋评李商隐,曾经说:“真正会看义山诗的人——看他‘春蚕到死丝方尽’一类诗的人——不应该对爱情有向往的,就像看《红楼梦》,只看宝哥哥爱林妹妹、林妹妹爱宝哥哥,就所见甚小了。真正懂得《红楼梦》的人都会发现,在这个爱情故事里显示出来的是天地的虚空和茫茫的悲感。”李商隐无疑正是这茫茫大地,浩浩夜空的独行者。
李商隐对爱情的态度是暧昧的,迷离的,矛盾的,诡异的,这无疑与他的遭遇有关,但也一定与他对世事的深刻洞察,和长久形成的世界观有关。这是属于理想者与悲观者的印记,所以张炜评屈原《天问》时说的这两句话,也适用于他:
“一个人绝望之后,往往寻求性的止痛药,然而往往无济于事。”
“一个民族,一个人,当开始选择这一止痛药的时候,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末路了。”
末路都遭阻断,这是一种什么境况?已经不相信爱情,还不断地写情诗,感动自己,感动别人,这会是一种什么心境?
李商隐已经落水,爱情不过是他的救命稻草而已,这悲哀到此已无法描述。
所以,此时的李商隐难免就会对一切怀疑,一切悲观,尤其对生命的不可捉摸,不可掌控。所以他也就会不断地留下这类诗句:春花烂漫时,突然说“莺啼如有泪,未湿最高花。”本已经在感叹“秋蝶无端丽”,却还要缀上一句“寒花只暂香”。
他就是说神仙传壶公的故事,都会说:“壶中若有天地,又向壶中伤别离。”
李商隐诗中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,天下第一,那就是“无端”。像什么“锦瑟无端五十弦”、“今古无端入望中”、“云鬓无端怨别离”、“秋蝶无端泣”、“秋蝶无端丽”等等,如花落满地。这个无端,便是他最显著的特征。
李商隐的这种无端之感,龚鹏程最懂,他曾说:“无端是什么?无端就是没来由的,没有理由可说的,换言之,就是对整个世界莫名其妙所从来而兴起的一种悲哀,这种悲哀是历史上特殊敏感的诗人所具有的特殊生命的情怀。”
如此这般,那么他的人生,无疑就是无端、有端的双重结果,那么李商隐身上的宗教气息,自然就会更加浓厚——红尘俗世一旦无望,这是常有的事。
而之所以要说更加,这是因为李商隐很早就曾在玉阳、王屋二山学道,他的忧虑气质、佛道之心仿佛天生,他的“无端”之求,以及对生命巨大而深切的关怀,在厄运未来之前,就已经有了。
李商隐的宗教生涯,有两件事特殊不同,这最能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。
第一:别人的向道向佛,是为长生不老,超越生命恐惧,追求极乐,功利心极强,而他不是。神仙之境他当然也很向往,甚至还自以为自己很有神仙气质,但他那神仙却可能只代表某种境界,神仙本身,他是不信的,曾一再质疑、挑战。
比如他写西王母:“瑶池阿母绮窗开,黄竹歌声动地哀。八骏日行三万里,穆王何事不重来?”
西王母曾经祝福穆王,“以子为寿”,但穆王却死了。八骏再快,穆王也来不了了,你还说什么神仙,什么长生不老?
第二:李商隐晚年转向佛教之时,却是唐武宗灭佛之时,唐朝佛教最衰微之时,这种事非大虔诚、大英勇绝不可为。更重要的是,那时的道教佛教斗争激烈,几乎水火不容,他偏偏只管两家都信。
李商隐当初因为婚姻,就背负忘恩负义之名,令朝中两派都对他不齿,这一次,他又是两头不讨好,只管两头不讨好。那么,这说明了什么?
无端,没来由,没理由,天生对生命有无端忧虑、质疑、探求,这自是一种伟大的气质,人类长大的基础,人类的来路与出处。李商隐和杨朱、阮籍,归根结底,都只对神渺的世界,深奥的生命,灵魂的安置着迷,他们作为政治人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学者,从来是为自己活,也是为别人活,为世界活,他们不管遭遇了什么,如何孤独痛苦悲哀,都不曾麻木、苟活、变质,他们哪怕到了晚年,也还在求真,求道,寻路,他们开始不只是为个人现实利益,最终更早已不在乎现实利益。
人类社会与生命的无限丰富、复杂、真实、虚幻,透过屈原伟大的《天问》,呼啸而来,宗教本关乎天地人的全部,那也是一部《天问》,李商隐的由道教转佛教,亦道亦佛,这既是又一种末路挣扎,又是新的探求,新的拯救。屈原《天问》的关怀、无端,宏大而没有尽头,其根本所求并非自身安宁,而是永世的解决、改变,他们这类人的伟大在于此,孤独、痛苦也在于此。
因为他们所代表的,原本就是人类的代价。
这里当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成功,根本不可能成功,但重要的却并不是成功,永无休止的设问与探索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,所以李商隐们的悲剧性格、虚幻感,怎么说,都是一种卓越的特质,一种巨大的心力。
悲剧性格也是一种沉迷性格,他们这种人的历史,永远都不会是愉快的历史,但历史的愉快,却一定由此而来。
这具体到李商隐的全部,便是:
政治不可靠,神仙不可靠,爱情不可靠,得到即失去,美丽即衰败,一切都那么荒谬,那么难以确定,李商隐即因此而哭——“东西南北皆垂泪,却是杨朱真本师。”他虽然自比杨朱,却把杨朱这歧路彷徨,歧路痛哭的意象几不知扩大了多少倍。
李商隐的哭,更多是来自生命之爱,关于生命本身,所以龚鹏程才会说:“李商隐的诗是人生普遍性的悲哀,这种别离是与一切美好事物的别离……李商隐对时间飘忽的感觉非常敏锐。”
因此,杨朱的歧路之哭,是十字路口错半步就可能差之千里、万劫不复的痛苦焦虑所致,是对于歧途的恐惧焦虑所致,是因人生无常,歧路离别的伤感、伤痛所致,阮籍之哭,则干脆是环境恶劣,可能有限,根本没有路。而政治、宗教、情感一概探过的李商隐,具有非常自觉性的李商隐,却是因为穷尽眼前所能,满眼虚幻而哭,因为极爱而哭。
但是他却依旧在这四大皆空中寻找各自可能,不死不休,别人是一面热爱生活,一面不想活了,他是一面不想活了,一面热爱生活,热爱生命,热爱真理,热爱世界。
张炜评屈原,曾说:“伟大的关怀才有伟大的迷惘,无穷的追问才导致了迷惘。然而这迷惘,比起墨写的历史却显得更加睿智和清晰,而且光华四溢,美不胜收,天地万象囊括一体。”
同样的,伟大的活力才有伟大的痛苦,高端高洁的追求才导致了绝大痛苦。如此,这哭声所体现的,便正是生命的轰轰烈烈,蓬勃不屈,灿烂光华,人类历史孵化、再造的来路。因此,这史上三大男人之哭,总而论之,最终体现的便是这种意义:
他们只有心情的荒凉,而无心灵的荒凉,虽个人遭遇不堪,目光投注的却仍是整个世界,虽不免悲观、失望,但理想性永在,他们追问的人生,远非现实功利那么简单,他们的处理方式,其实有特别的着陆点,他们是为自己而哭,也是为世界哭,为理想哭,为美好哭,他们的哭,归根结底,是不甘,是为了自己和他人更好地活着,为了世界更好地存在。
如今经常看到有人问,我们为什么没了真正的大师?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。我们已经失去了更高的关注点、投注点、好奇心、想象力、理想、情怀、关怀、浪漫、悲悯,成了技术产品、功利机器、蜗居动物,惟从之于风,不再是火。
崇高辽远的设问、探求不再有,“东西南北皆垂泪”不再有,历史的绝响,居然是三个男人的哭。男人之哭,非由阮籍而尽,难道可由李商隐而尽?这从个人遭遇,时代遭遇来说,或许是好事,但对整个人类来说,却可能是一种萎缩。
“哭起来吧!”这样说当然是一种病态,但“时间可以抹去大地的创伤,却抹不掉心头的恐惧和疑问”(张炜),未知永在,矛盾永在,选择永在,美好的追求、得失的反复永在,歧路彷徨永在,安顿的需要永在……它们环绕千古,躲不掉的,人到底不是鹌鹑。
我们不能“无端”,至少可以“有端”,不能高远,至少不该下沉。
文 | 九鸦
图 | 网络
本文作者:九鸦人物(今日头条)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toutiao.com/a6699725115183071747/
声明:本次转载非商业用途,每篇文章都注明有明确的作者和来源;仅用于个人学习、研究,如有需要请联系页底邮箱
- 搜索
-
- 06-08同样是异族侵犯面临亡国,为何唐太宗和宋真宗的反应竟天差地别?
- 06-08历史的十字路口,有三个男人在哭
- 06-08秦始皇曾经给中国取了个名字,不管时代怎样变迁,一直沿用至今
- 06-07张仪连横破合纵————忽悠楚怀王
- 06-071867年沙俄以720万廉价卖掉阿拉斯加,百年后为何又要卖北方四岛
- 06-07慈禧的第一位小车司机,大臣觉得有损礼仪,要求他跪着开车
- 06-07清朝初期八旗议政最具影响力的决策机构--议政王大臣会议
- 06-07只要利民就行——春秋精美故事100篇之(45)
- 06-07张作霖16岁时差点饿死,一个寡妇好心救他一命,他发达后这样报答
- 06-07东晋名妓,艳压陈圆圆,丈夫去世割耳守节,16岁守寡到老
- 999℃河南这些高校教师入选中原教学名师 有你母校老师吗_河福州三中家校互动平台南
- 999℃河南iq过大河省人社厅公布上半年重大欠薪典型案件_河南
- 999℃河南人注意!公安部发布B级通缉令悬赏缉拿他_河财经927在线收听南
- 999℃平顶山警方抓了百余名“成征服者雷萨赫尔顿功人士” 揭秘他们人生巅峰黑幕_河南
- 998℃河南曝光违法超限运输企业名单 济源一企业仨月违法学什么容易找工作861次_河南
- 998℃郑州南站项目年内开工黄花菜的功效与作用 城区几条河流3年内能游泳_河南
- 998℃2nbaqq空间免费代码017河南高考分数线揭晓 一本文科516理科484_河南
- 998℃紧急预警!河南10地有雷洛浦公园水怪电活动!局部雷暴大风_河南
- 998℃郑州全市铁征服者雷萨赫尔顿路沿线违建拆除逾八成 本月15日前完成拆违_河南
- 997℃今日券商“买入”十烊千玺萌大金股(0215)_财经头条
- 06-06秦淮八艳之柳如是:她是明朝的第一名妓,史学大师花10年为她立传
- 06-06“四大洋”还是“五大洋”?南冰洋究竟是不是“第五大洋”?
- 06-06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纯友谊?孔子的10字箴言,讲出了他的本质
- 06-06千年前法国,俄罗斯,意大利均属于中国版图、还有如土耳其
- 06-06明朝的一场神秘爆炸案,两万多人去世,死者皆是赤身裸体
- 06-06古蜀国的消失与它的三王二帝,蚕丛、柏灌、鱼凫,杜宇、鳖灵
- 06-05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,管仲找到了正确的路,他是如何做到的?
- 06-05遗落民间的非遗瑰宝:陕西周至竹马
- 06-05“国学大师”章太炎,真真是民国第一学术泰斗
- 06-05看看同治皇帝16岁时的奢华大婚,是清朝的“中兴”还是回光返照?
- 标签列表
-
- 河南 (386)
- 历史 (328)
- 平顶山 (284)
- 郑州 (157)
- 清朝 (97)
- 不完美妈妈 (92)
- 明朝 (90)
- 政治 (65)
- 曹操 (62)
- 三国 (62)
- 文化 (62)
- 唐朝 (60)
- 经济 (60)
- 食盐 (54)
- 宋朝 (53)
- 河南省 (53)
- 中国历史 (50)
- 刘备 (50)
- 刘邦 (49)
- 日本 (46)
- 诸葛亮 (46)
- 秦始皇 (45)
- 汉朝 (44)
- 朱元璋 (44)
- 民警 (43)
- 北宋 (40)
- 蒙古 (37)
- 暴雨 (37)
- 平顶山市 (36)
- 南宋 (35)
- 交警 (35)
- 西汉 (33)
- 项羽 (33)
- 唐太宗 (32)
- 康熙 (31)
- 秦朝 (30)
- 关羽 (30)
- 美女 (30)
- 三国演义 (28)
- 服装 (28)